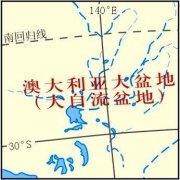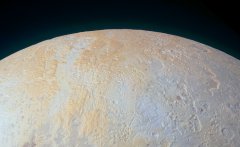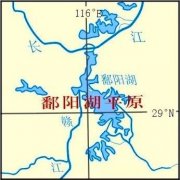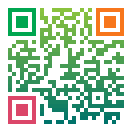囚犯·开拓者·现代人
班机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飞行。渐渐地,穿过云层,降低了飞行高度。我斜靠舷窗,看一看陌生的南半球大地。展现在眼底的,是碧草如茵的广阔牧场,蜿蜒如带的河流和公路,显露红褐色斑点的丘陵的山岗和低矮的农舍。渐渐地,看到了海湾,看到了湛蓝的南太平洋。接着来的是大城市上空特有的暗黄的尘雾,透过尘雾的空隙,是林立的高楼,密密麻麻的街道。飞机急速下降,悉尼到了。
“好漂亮。”我自言自语地称赞一句。我的邻座是一位从香港来的经纪人。他经常往返于香港与澳大利亚之间,是这国泰航空公司班机的常客。悉尼对他已是司空见惯,但他要对我这位北方来的同胞表示一点关切,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淡淡地说:“你能相信吗?这是个囚犯建立的国家。”
我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微微一笑,没有搭腔。这位先生的话有一点点历史依据,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而且可能由于在香港生活久了,多少还接受些英国人传统观点的影响。
是的,二百年前,世上人对南太平洋中这块奇异的大陆是充满神秘感的。
在英国人踏上这块土地以前,好几个国家都有人说曾经在航海途中看到过它
的影子。但是说来说去,在人们心目中,那是一个近于蛮荒的世界,没有可
耕的土地,没有可以使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野草丛生,爬虫遍地,其中若
有人迹,也仅是茹毛饮血的黑色土著。而当时,英国已经发明蒸汽机和织布
机,法国的卢梭已经完成被恩格斯认为有辩证法思想的《民约论》,德国的
歌德已经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国的曹雪芹也已写出《红楼梦》。
1770 年4 月的一天,一艘远航船犁开太平洋的波浪,驶近澳洲东海岸,
登上一座杳无人迹的小岛,从此结束了这个神奇大陆与世隔绝的历史。
一位澳大利亚朋友陪我凭吊了这座小岛。它坐落在悉尼南边15 公里的植
物湾(Botany Bay)。与其说它是座小岛,不知如是一块大岩石更恰切些。
这就是当年库克船长(James Cook)最先靠岸的地方,现在成为纪念地和旅
游点了。人们来到这里,自然会将遐想投向200 年前的那一天。
那一天是4 月17 日,库克上校和他率领的远洋航船结束在新西兰的探险
和对日蚀的勘测,准备返航回国。可是风向突然变了,吹斜了航船的方向,
将他们送到一个小小的港湾。同船的科学家班克斯爵士(Joseph Banks)在
日记里记着:
“⋯⋯黄昏时分,我们在港湾北部一个小岛上登岸,打算寻找一些贝
类。”
他们并没有找到太多的贝类,却找到一块大陆,一块可以同1492 年哥伦
布发现美洲相仿佛的新大陆。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天是澳洲新纪元的第一
页,这是明显的殖民主义者的眼光。即使没有这一天,没有库克船长和班克
斯爵士这艘船,世界终久也会发现澳洲的。澳洲并不是人类绝迹的荒岛,它
那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但是,无论如何,1770 年4 月17 日这
一天,总还是值得纪念的。所以在小岛上至今还立有一块碑石,刻着班克斯爵士那段日记。日记作者还写道:
“四野碧绿葱翠,树木丛生⋯⋯还有大片的青草地,泥土夹有洁白的细
沙⋯⋯”
他们发现了原来认为不可能孳生的植物,就把这个小小港湾称为植物
湾。班克斯再一观察,似乎还可以种水稻,栽果树,甚至还可以成为优良的
牧场,不禁大为惊喜。本来,库克上校临离开英国前,就奉到一纸密令,要
他相机寻觅太平洋中那个传说中的大陆。现在终于意外地找到了,于是他们
将详细勘测后的一块土地,命名为“新南威尔斯”(New South Wales)并且
正式宣布它是英王乔治三世的属地。澳洲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此后十多年中,这块孤悬南太平洋中的属地,仅仅成为英国植物学家科
学研究的领域。路途太远,船只一去一回差不多就要耗费近两年时间。一般
人简直认为那是另一个世界了。直到1787 年,美洲独立了,英国政府再不能
按传统将囚犯流放到新大陆去,国内监狱人满为患,于是想起这个遥远的“新
南威尔斯”。殖民老爷们认为那块土地面积大,离英国本土又远,既不会给
他们带来麻烦,又不用担心犯人逃逸,岂不是上帝所赐的一个理想的“流刑
殖民地”?那年 5 月,海军上校阿瑟·菲力普(Arthur Phillip)率领由11
艘船组成的船队,号称“第一舰队”,从英国启程,浩浩荡荡地开到澳洲来。
船上载有700 多名囚犯,还有两百多名海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共1475 人。
他们呆呆地望着滚滚浪涛,神情悒郁,心情沉重。既不知道要去的是个什么
样的地方,更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返回英国。“第一舰队”在大西洋、印度洋、
太平洋航行了8 个多月,才于第二年(1788 年)1 月26 日到达植物湾附近的
杰克逊港登岸,在那里插上英帝国的国旗。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悉尼城。
当时,包括费立浦船长在内,谁也不曾想到日后会在这儿建立一个国家。1
月26 日这个日子(在南半球,正是赤日炎炎的夏季),现在已成为澳大利亚
的建国纪念日。
现代的澳大利亚人,比如我在这次旅行中所结识的朋友,从政府官员、
大学教授、作家、记者、艺术学校教员、大学生到出租汽车司机、失业青年,
包括陪我到植物湾游览的那位青年朋友,谈起这一段早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在
澳洲的历史,他们倒都不讳言那些囚犯和殖民者的祖先,也不隐瞒早期屠戮
当地土著的血腥史实。
有一位教授说过:“坦率说,我并不认为最早来澳大利亚的囚犯都是凶
恶的坏人。你知道英国过去的法律是极其苛严的,甚至到暴虐的程度。偷一
点小钱、偷一片面包,都要定刑的。有些人为了吃饱饭,干了触犯刑律的事。
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另一位记者说过:“有些囚犯在澳洲受到的待遇,比在英国本土还严酷
得多,塔斯马尼亚岛上有个亚瑟港,那里还保留当年拘押囚犯的牢狱,关在
那里的,据说是案情最重的犯人。牢房里陈列着铁镣、铁链和各种刑具,牢
房外面只有一条小路通到外边,那时候这条小路由许多恶犬把守着,谁想逃
走,只有一条死路。”
还有一位作家对我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些英国皇家
军队怎样屠杀澳洲土著的事实。土著们的外表会使你大吃一惊,但他们的性
格是善良的,从不主动地伤害外来人。对他们开枪,实在是残酷的、可耻的,
是我们澳洲历史上极不人道,也极不光彩的一页。”
无需这位朋友详细描述,我完全相信他这几句最简练而又包含丰富内容的话。
比较起来,澳洲朋友愿意更多谈的,是早期的开发者们的事迹。因为50
年后,到1840 年,向澳洲流放囚犯的制度便已废止。陆续从英伦三岛远渡重
洋而来的,是所谓的“自由人”。当他们靠在远洋轮上凭栏遥望东方时,大
多数人都充满了欢乐的幻想,好像那个神奇的澳大利亚是个遍地黄金的地
方,只等自己去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装满了。不料一上岸,一住下来,就发
现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是陌生的,崎岖的,而且是神秘莫测的。他们渐渐发
现,这块土地并不像班克斯报告中描写得那么美妙。气候炎热,空气干燥,
雨量少得惊人,山峦是光秃秃的,岩石上像火烧过似的寸草不生;河流是干
涸的,龟裂的土地像渴倒的野牛躺着直喘气。有的鸟叫起来使人毛骨悚然,
有的鱼怪得使人不敢吃它。
这样的天地,人怎么生活下去?
大约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吧,人类总有一种非凡的适应力,
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回头的路已经断绝了,要想生存,除了咬紧牙关、
埋头苦干以外,连上帝也不曾为他们准备第二条路。
开拓者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终于赢得向澳洲大陆自然界艰辛搏斗的
第一个回合。
以后,发现了煤矿,培育了西班牙种绵羊,英国纺织厂里开始用澳洲羊
毛。正赶上英国产业革命的浪潮,到处呼吁原料,澳毛成为十分吃香的物资,
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奠定自己的地位。以后,又培育了乳牛,种植了小麦和甘
蔗。到19 世纪初叶,金矿的发现兴起了连续几十年之久的淘金热。“到澳洲
发财去!”成为最有诱惑力的口号。成千上万的人流从英伦三岛涌向澳洲:
雇工、技师、医生、会计员、教师、乡村小作坊主,以致无业游民。从1851
年到1857 年7 年中,就移入 40 万居民。 19 世纪中叶起, 30 年中,澳洲
人口由 100 万猛增到300 万。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80 年来,
它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工业交通不断发展,矿产资源不断发现和开采,
新的城镇不断建立,终于使世界对它刮目相看了。
我漫步在植物湾头,望着南太平洋的万顷碧波,想象那位库克船长当年
冒险上岸的光景。突然又想起前几天在墨尔本菲兹瑞公园曾经参观过这位船
长的故居。他的故居本应在英国约克郡的灰堤贝,怎会到墨尔本来的呢?原
来是澳洲人为了永久地纪念这位200 年前发现这块土地的人,就商请上校家
乡的政府,将他故居那座小屋,整个儿搬到澳洲,让船长从此定居墨尔本。
小屋的每一块砖瓦木料,包括铁钉、螺丝,一点不漏地从原地运来,再照原
式原样重建。据说屋前攀搭着一株常青藤,也是库克船长少年时常常抚摸的
旧物。后代的澳洲人,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
我们离开植物湾,驱车回悉尼市区,过了那座被人戏称为“大衣架”(因
为它外形很像一只硕大无朋的衣架)的大铁桥,就进入市中心区。从荒寂的
海滩小岛回到繁华嘈杂的高楼群中,好像一下子穿过了200 年的历史风雨。
海涛声,呐喊声,呵责声,鞭打声,野兽咆哮声,碎石铺路声,篝火毕剥声,
第一列火车和铁轨的撞击声、港口轮船的汽笛声⋯⋯全都交织在一起。囚犯
的呻吟,开拓者的叹息和祈祷,被当代澳大利亚的谈笑声所淹没了,也许真
的只有植物湾那个小岛,还有那位记者说的亚瑟港的牢狱遗址,还残存一些
200 年前的痕迹,其他都不复存在了。我在悉尼、堪培拉、墨尔本看到的,
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既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也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即使赛马、夜总会和激光游乐场,也无一不具
有现代的声光色彩。古老的艺术进了博物馆,古老的装束和家具成了店家招
待顾客的广告。比如前天同两位新闻界朋友一起吃饭的水上饭店,那布置宛
似一艘海船,进门上楼,就进了货舱,堆着木箱、粗麻绳和好似正要卸下的
麻包。桌椅、船栏都用竹木和棕绳,侍者都穿着白衫黑裤的海员衣,连菜单
都印在古拙的薄木片上。若不是楼下有电子音乐声和来往的小轿车声,你会
以为是在一艘十九世纪初从欧洲来的远航船上。人们到这里,并没有丝毫的
怀旧之情,纯粹是由于新鲜,就同他们走进一家日本饭馆或土耳其浴室一样。
是的,现代的澳洲人不会忘记他们的祖先,那些胼手胝足、艰苦创业的
开拓者。但是他们想得更多的却是今天和明天。当别人问起他们的家谱时,
他会告诉你前几辈来自苏格兰的什么山什么河,或是英格兰的什么郡什么
村。如果你不问,他们也就绝口不提。要说,就是:
“我是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人!”
我在好几个宾馆的小卖部和商店、市场里,都看到出售一种汗衫,上面
印有澳大利亚的地图轮廓,还有一行字:
“I Love Australia(我爱澳大利亚)!”
这就是当代澳洲人的心!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文中有些文字或数据已经过期失效,仅供学习备课参考!
电脑版地址:http://www.cgzdl.com/shuku/242/9626.html
手机版地址:http://m.cgzdl.com/shuku/242/9626.html

-lp.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