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去来”与澳洲土著的文明
前些日子,整理杂物,翻出一件中间弯曲两头细长的铜器,上面分别铸有澳洲的大袋鼠、考拉,还有澳洲土著人的头像以及他们使用的投枪和盾牌等图形。这件铜质的小工艺品是我访问澳大利亚的纪念品,它是澳洲土著民族使用的一种武器的仿制品。
这种独特的武器,名叫“飞去来”。由这件“飞去来”,不禁想起年前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情景,但我的思绪更多地追索着在那块广袤大地上生活的一个多灾多难的古老民族⋯⋯关于澳洲土著使用的“飞去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做“飞标”(boomerang),对它的解释是:“弯曲形投掷尖刺武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多在狩猎及战争中使用之。飞标有两种,飞标式的棒状武器则是多种多样的。可飞回的飞标(其名源于新南威尔士州的图鲁瓦部落)体轻而细,掷出时可保持平衡,长约3—75 厘米,重约340 克,其形状有大弯、小弯以至平直的两个边,成一角度,在制作时或在灰烬中加热之后,将两端各扭向相反方向。可飞的飞标曾在东澳大利亚及西澳大利亚流行,有时作为玩具,用于比赛;有时猎手用它模拟飞鹰,以驱逐鸟群,使之进入悬挂在树上的网里。可飞回的飞标是由不会飞回的飞标发展而成,后者在飞行中会突然转向⋯⋯”澳洲土著民族使用的可飞回的飞标就是“飞去来”,也有的书上称做“飞去来器”。
真正的“飞去来”,是用硬木片作的,样子像镰刀,它的奥秘全在于硬
木片的形状,在空中飞驰时呈螺旋似地转动,所以当它被扔向目标时如果没
有击中,还能飞回到投掷者的位置。这当然是需要非常熟练地掌握它的要领。
因此,有的民俗学家考察了澳洲土著民族的“飞去来”,认为它应用了
复杂的物理规律,由于每端有不同的平面,它的原理颇似螺旋桨的运动形式。
美国作家、著名记者约翰·根室在他的最后一部世界内幕书——《澳新
内幕》中,引述了一位探险家所见到的澳洲土著民族是怎样表演使用“飞去
来”的:
因为是为了表演,那些土著将一只死老鼠挂在矮树丛里,那个年长的土
著男子宣称,他要用飞去来打那只死老鼠,而且要故意不打中。”他把身子
卷成一团,猛然一甩。只见飞去来从左边很远的地方擦着地面打了出去,接
着升到15 或20 英尺的高度。在往回飞的那一刹那,飞去来好像停住不动一
般。接着便继续往回飞,这时它降低到膝盖的高度,从死老鼠上面仅仅一英
寸的地方掠过。这个土著往边上跨出一步,便从空中把飞去来收了回来。
这段描写令人想起精彩的杂技表演。
据记载,当第一批欧洲人踏上南半球陌生的大陆——澳大利亚,和澳洲
土著接触后,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飞去来。英国海员菲利普·帕克·金
曾经写道:“飞去来是件很可怕的武器。这是一片又短又重的弯曲形木头,
用手投出去,在空中旋转推进,投法极为高明,以至只有投它人的人才知道
它要落在哪里。”他还说:“土著成功地用飞去来打大袋鼠。”依我看,飞
去来这个武器更多是用来打猎而不是用来作战的。”
这个英国船员据说是第一个向世界报道飞去来的欧洲人。从此,澳洲土著的武器不仅为世人所知,而且万万没有料到,飞去来如今已经风靡全球,
成为人们健身的一项体育活动器械,尤其受到青少年的欢迎。
只不过,人们玩耍的飞去来,多是塑料制作的。
我是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的首府——帕皮提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的悉
尼的。即使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飞机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空也飞了整整
5 个小时,澳洲的遥远、远离其他大陆,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虽然澳洲大陆土地辽阔,地形多种多样,兼之气候温暖,动植物种类繁
多,适合人类生存,但是在欧洲人踏上这块陆地之前的漫长岁月,澳洲土著
民族并没有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取得惊人的进步。据有关资料介绍,在18
世纪欧洲人“发现”澳洲之前,在这块大陆生活的澳洲土著约有30 万人,分
属500 多个部落。古人类学家通过发现的古人类头骨等化石埋藏,证明澳洲
土著的祖先早在4 万年前便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可是,在长达数万
年的漫长岁月,澳洲土著依然停留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过着石器时代的
原始人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
不论是澳大利亚南部塔斯马尼亚岛上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的土著,还是
大陆上有着深棕色皮肤、个子稍高的土著,他们既不会农耕,也不会畜牧,
他们不懂得制作原始人的陶器,也没有固定的家园。有的研究者说澳洲土著
是些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为了采集食物,不得不四处
奔走,用飞去来器、木棒、长矛和各种打磨的石器猎获大到袋鼠小到蛇、蜥
蝎,几乎是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在沿海地区和湖泊附近,土著人也用简
陋的方式捕鱼。此外,他们也采集植物的种籽、果实和块茎。并且,澳洲土
著懂得使用火,而火的使用和熟食,在人类进化的链条上是极重要的一环。
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介绍得知,澳洲土著结成人数不等的氏族部落,大的
部落有几千人,小的部落仅有百把人。他们和其他大陆的原始民族一样,以
各种动物或自然现象为部落“图腾”,并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而图腾
崇拜和具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岩画,是他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文
化财富。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由于澳洲大陆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地理环境,澳洲土著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不必担心外来民族的
侵入,也没有战争打扰他们安宁的生活,甚至自然界也不存在太多凶猛的野
兽给他们以伤害,而澳洲辽阔的土地不乏可以裹腹充饥的食物,他们如同生
活在和平安宁的伊甸园,但结局怎么样呢?结局是发展的停滞,文明的衰落,
以及民族的衰弱,而无法抗拒外来的冲击。这,恐怕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则吧。
由此观之,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同民族相互之间的
撞击和交融而焕发活力的。流血的与不流血的,野蛮的与文明的,战争的与
和平的,形式多样,但不管怎样,唯有接触、渗透、融合、交流,才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而静止的、封闭的、死水一潭的社会终将走向衰亡。这,当然
是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言。
正是如此,一旦欧洲人以贪婪的殖民主义者的目光投向澳大利亚的土
地,长期与世隔绝的澳洲土著,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我在堪培拉住了几夭。堪培拉给我最深刻不过的印象是她的静谧、温馨
和乡村的闲适。推窗望去,满目是浓荫的参天大树,以及林带之间柔软如绵
的草地。造型各异的民居悄然藏在树林后面,小汽车也是悄悄地匆匆来去,
唯恐打破了城市的安宁。虽然也有新落成的议会大厦,还有政府办公楼、博物馆等现代化建筑,但你很难把她和首都或是现代化城市联系一起,在我的
印象里,堪培拉只不过是个大村庄。
堪培拉有个人工湖,用城市设计师的名字命名,叫格里芬湖。湖上有水
柱高扬的喷泉,阳光下彩虹飞舞,煞是好看。我在湖畔散步时,发现那绿茵
茵的草地有座用水泥护栏圈起的巨大地球仪,在它金属的空心圆球表面,除
了交织的经纬线和地球各大洲的轮廓,还有库克船长的一条弯弯曲曲的航行
轨迹。这是为表彰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200 年而建的一座特殊的纪念碑。
说起澳洲大陆的发现,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从欧洲人的立场提出的,因为
对于澳洲土著而言,他们在这块大陆上生存了少说也有一万年,何来发现之
说。这就如同我们常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对于美洲的印第安人,岂
不是笑话。
欧洲人对澳洲大陆的发现,始于17 世纪,最早踏上澳洲大陆的是荷兰
人。1606 年,荷兰航海家威廉·扬茨乘“杜夫根号”船到达澳洲北部的约克
角;1642 年,另一位荷兰航海家塔斯曼发现了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
岛,以后又发现了澳洲西海岸。不过,他们的发现并没有多么大的影响,甚
至还弄不清楚所到之地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未知的南方大陆”。
到了18 世纪,英国人加快了寻找地球上“未知的南方大陆”的步伐。1768
年8 月,英国著名航海家、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奉命率“努力号”舰驶向南
太平洋,目标是寻找南方大陆,终于在1770 年4 月登上了澳大利亚东海岸,
同行的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在这一带海岸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因
此这一海湾被库克命名为植物湾。
库克船长比起荷兰人发现澳洲的时间虽然稍晚,但他是真正调查这块陌
生大陆的第一人。库克走遍了澳大利亚2000 多公里的东海岸,绘制了精密的
地图,对这块大陆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除此之外,库克船长不仅把英
国的米字旗插上南方大陆,而且宣布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占领了这块原本
属于澳洲土著人的家园,于是澳洲大陆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正是格里芬湖畔库克船长发现澳洲200 周年纪念碑的来由。
1788 年1 月26 日——这一天后来即是澳大利亚的国庆节——由6 艘运
输船、4 艘海军补给船和1 艘海军供应舰组成的“第一船队”,经过半年的
艰难航程,驶入今天的悉尼湾。这是一支特别的船队,除了211 名海军官兵
和部分官员、牧师、军医及他们的眷属,其余700 多名乘客都是英国各地监
狱关押的犯人。他(她)从英国本土远渡重洋,被押送到遥远的澳洲大陆,
等待他(她)们的是远离故国的流放生涯。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澳洲早期
流放犯的艰苦劳役和他们对澳洲开发的种种业绩,也无法描写当年发生在流
放地的黑暗内幕。我所关注的是,当英国人不断地将大批罪犯运往澳洲,不
断地扩展他们的地盘,侵占越来越多的土地,澳洲土著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据约翰·根室提供的资料,欧洲人来到澳洲后,他们对澳洲土著进行了
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但是关于这一桩桩血腥的残酷的历史事件,澳大利亚的
历史学家却视而不见,讳莫如深,往往是一笔带过。我曾经到过澳大利亚南
部的塔斯马尼亚岛,如今是塔斯马尼亚州,这里是皮肤黝黑、个子稍矮、头
发卷曲的塔斯马尼亚人的居住地,当初至少有4000—5000 人。不过,我在岛
上并没有见到一个土著人。据约翰·根室在《澳新内幕》一书中指出:“世
界上唯一的一次把整个人种彻底灭绝的事就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在那里,两、
三千名土著被四处追杀,最后只剩下200 人左右,又被押到邻近的佛林德斯岛去。到1874 年,只有40 人残存,最后剩下的16 个人被送回塔斯马尼亚,
其中死得最晚的一个名叫特罗卡尼尼,死于1876 年。”也就是说,在19 世
纪70 年代,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已被白种人斩尽杀绝了。
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整个澳洲大陆的一个缩影。这是
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当欧洲人不断开拓殖民区,营建定居点时,他们不仅将
土著人从土地肥沃的沿海地区驱赶到内陆荒凉贫瘠的地区,而且制造了一桩
桩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1857 年发生的弗雷泽哈姆惨案,是2 名英国人引起
的。这两个无赖从弗雷泽哈姆出发,到附近的土著村落昆加里强奸了2 名土
著女子。在外狩猎的土著男子闻讯后追往弗雷泽哈姆,惩罚了肇事的凶犯。
这时,英国人从各处汇集弗雷泽哈姆,仗着他们有先进的武器,将昆加里以
及附近土著村落团团围住,竟然惨无人道地将近2000 名土著人,不管男女老
少统统杀死⋯⋯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在南美洲的所见所闻。当年欧洲人踏入美洲大
陆后,当地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一如澳洲的土著一样遭遇到极其悲惨
的命运。约翰·根室这位美国记者、作家不无愤怒地指出:“白人得寸进尺,
为攫取更多的土地开始实行‘驱散’,这是大屠杀的一个委婉说法。他们四
处‘猎取土巴佬’取乐,这是他们周末的一种快活的游戏。警察也参加进来,
打死那些偷羊的和从不久前还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上拿走些物产的土著,以
杀一儆百。搞得最凶的时候,他们竟用下了毒药的食物来毒死这些‘害兽’,
杀掉他们,剥取他们身上那种具有依尔莎·科赫风格的刺花的皮肤⋯⋯”
殖民主义者就是这样毫无人性地消灭着澳洲土著,他们的行为连禽兽都
不如。他们的罪恶行径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最好的注脚。
据有关统计资料,到19 世纪末,澳洲大陆所剩下的土著仅6 万人,其中
还有不少混血种,而1788 年居住在澳洲的土著有30 万人。
人类,只有在美好而宝贵的东西失去之后,才会在事后追悔莫及。
澳大利亚建国已经200 多年,澳洲土著的境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
较大变化,如通过了一些保护土著的法律,划定土著的保留地,等等,但土
著问题至今仍是澳大利亚国内一个棘手的敏感问题。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澳洲土著人口锐减以及他们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
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澳洲土著所创造的原始文明的价值,他们竭力抢救
这些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澳洲土著研究所的专家们希望趁着土著文化还没
有消失之前用影片、录音带和其他技术手段将它保存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工作。
人们现在发现,澳洲土著民族并非殖民主义者所宣扬的是野蛮的、落后
的,他们在艺术、文化、音乐、舞蹈、诗歌乃至宇宙观等方面,都取得了相
当高的成就。作为澳大利亚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土著文化是最卓越的富有创
造性的,也是最具世界意义的。
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澳大利亚北部、西北部发现的石窟画,也就是
岩画,其数量数以千计,分布在一些洞穴的岩壁和穴顶。岩画题材多种多样,
既有神话传说,也有土著人劳动、生活的情景和各种动物造型。特别是一种
澳洲土著所创造的透视画(也有的译成X 光图画),除了阿纳姆西部地区之
外,目前全世界尚没有第二例。这种岩画所画的飞禽走兽,不仅画出维妙维
肖的外表,而且画出躯体内部器官,像骨骼、肠胃、心脏等,仿佛土著画师
具有神奇的特异功能,能透视动物体内的构造一样。
澳洲土著的艺术还有树皮画,葬礼时用的彩绘柱、地面画、文身画和某
些有神秘意义的图画。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充满想象力和丰富比喻的诗歌,
土著的诗与歌曲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有原始的笛、枕鼓、牛吼器等乐器,还
有内容丰富、既是宗教仪式又有娱乐性质的舞蹈。因此,西方一些富有远见
卓识的学者认为,澳洲土著所创造的精美发达的文化,是一种适应环境而不
是使环境适应人的文化,是一种健康向上能满足人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意
义上,今天生活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人们,倒是应该虚心地研究土著原
始文明的精髓,从中也许不难找到非常有益的启迪和丰富的艺术灵感呢。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文中有些文字或数据已经过期失效,仅供学习备课参考!
电脑版地址:http://www.cgzdl.com/shuku/242/9624.html
手机版地址:http://m.cgzdl.com/shuku/242/962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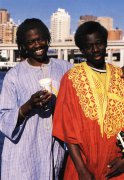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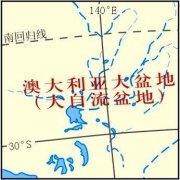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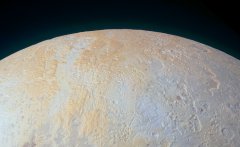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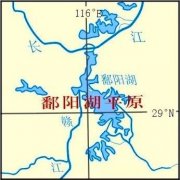
-lp.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