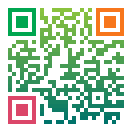北非之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
自从脚踏上埃及的国土,我时常记起唐朝诗人李益的绝句: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是什么东西触动我想起这首诗的境界?作怪的总是沙。不信请看,那大片大片的沙漠地带,月色一映,白茫茫的,直是那满地霜雪。也有时,天边日落,你远远会望见一群羊,几只骆驼,散放在夕阳影里。牧羊的埃及人头上披着白巾,身上穿着宽大的白袍,对着晚风,呜呜咽咽吹着一种双管的芦管,那凄楚的声调,听了,不由你不怀念起远在千万里外的亲人。
不过沙漠还有神奇的另一面。有一回,我从地中海岸上的亚历山大港坐着车往开罗去,半路打开窗,一阵凉风扑到脸上:奇怪,好香啊。接着就看见前面路边上有两三个小姑娘,捧着大把的花,黄的、紫的、粉的,叫都叫不上名,拦着车叫卖。我望望车外,满眼都是荒沙,难得看见点绿颜色,从哪儿来的花呢?是不是沙漠深处还藏着什么秘密,这是值得探一探的。我就去探过一次。从开罗往西北走,一直走进西沙漠去。乍离开人烟繁华的都市,更感到沙漠的荒凉。有时候会发现几丛沙草,说灰不灰,说绿不绿的,模样儿挺憔悴。生物还是有的。有兔子,还有一种十分灵巧的小鸟,颜色像沙,跑得飞快,只是不知道它能从沙漠里搜寻到什么吃的。渐渐地,沙漠变得有点异样:四处显出斑斑点点的绿色,路两旁还栽着两溜树秧子,两三尺高,据说枝叶熬成药水,蚊子最怕,我们就叫它蚊子树。这当儿,车子在拐弯,迎面出现一块大木牌子,是蓝色,上面从右到左横写着阿拉伯文字:“沙漠中的天堂”。
进了“天堂”,四周围的绿色更浓,生机也更旺了。忽然间,眼前出现
一个新奇的地方:有干净明亮的房屋,清澈的水池,丝绒一样的草地,还有
盛开着洋海棠的花圃。
原来我已经来到埃及有名的“解放省”,这是“首府”。公共关系部的
经理把客人迎进他的办公室去。这个人叫罗持德,三十岁左右,上唇留着怪
俏皮的小胡子,说起话来也挺俏皮。大概从亚洲来的客人叫他格外高兴,他
像冷似的,对搓着双手说:“怎么样,朋友,还喜欢沙漠么?”
我说:“这种沙漠我倒喜欢。”
罗持德笑起来说:“要知道,朋友,这种沙漠是从野蛮的敌人手里夺来
的呀。”就指给我看桌上陈列的一块兽骨化石,接着又说:“这是古代的猛
蚂,从这一带掘出来的,千万年前,该是沙漠王了。你如果在三年以前来到
这里,你能看见的也无非是骆驼蹄子印,而今天⋯⋯”
在沙漠里称王的却是人了。说起来历史还短得很,不过是1954 年6 月起,
因为埃及的沙漠太多,人丁兴旺,才对沙漠发动了攻势。罗持德一开始就参
加到这支征服沙漠的大军里来。他本来是律师,生活富裕,却宁愿来跟风沙烈日就伴。
罗持德笑着说:“我爱沙漠,爱得要发疯啊!离开她,我一天也活不下
去。”
我笑着说:“你这话,可别让你妻子听见,她要吃醋的。”
罗持德把小胡子一撅说:“她还吃醋?我不吃她的醋就是好的。告诉你
实话吧,从来那天,我就跟沙漠结婚了,把整个肉体和灵魂都交给她,谁知
她后来竟又跟尼罗河结了婚。”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又道:“我们往常总
是说尼罗河是埃及的恩人,给我们鱼、米、野鹅⋯⋯谁也料想不到,一旦沙
漠跟尼罗河结了婚,沙漠会给我们生育出什么东西来。”
罗持德就领我去看沙漠的生产。这一带的方位大约在开罗到亚历山大港
的半路上,东边靠着尼罗河三角洲。一条叫“解放运河”的大水从尼罗河引
进干旱的沙漠,于是沙漠便怀胎受孕,开始繁殖起来。
看啊!那春麦,那蚕豆,那蓝靛,⋯⋯一大片一大片的,叫白沙一衬,
绿得更加动人。那芒果,那橘子,那橙子,林林总总的,尽管还不到开花结
果的年纪,却已经让人想象到那累累满树的金色的果实。还有那金盆一样的
向日葵,枝叶像笼着碧纱一样的树木,以及各色各样叫不上名儿的植物。我
看了不觉在心里嘲笑自己说:“你还总以为沙漠是不毛之地呢。”
我想的还要多。我们不是有两句巧语儿么:“骆驼钻不过针眼去,沙漠
上盖不起高楼大厦来。”人家就在沙漠上盖起楼来。不信请看那水泥管厂、
缝纫厂、橡胶厂,还有发电厂、冰厂、罐头厂、拖拉机站⋯⋯盖好的,没盖
好的,远近都是。
罗持德告诉我说,这里已经建造起几个崭新的村庄,将来要发展到几百
个,而那些工业区,就是明天的城市。
人呢,从四面八方涌来,都是年轻力壮的,抱着一个热烈的愿望。举富
爱德为例吧。她对我说:“我从大学毕业后,本来在开罗一家幼儿园做事。
我丈夫是个医生。我们不喜欢留在开罗,情愿到这儿来。我们在这儿很幸福。
因为我们懂得自己是在为未来贡献力量。”
富爱德是个很精明的妇女,穿着白毛衫,灰裙子,眉目间透着严肃,又
透着温柔。是她领着我去参观一个新建的村庄。我问她道:“你能看见你说
的那个未来么?”富爱德淡淡一笑,没说什么。这时正是中午,许多人聚集
在村子当中一座清真寺里,有坐的,有跪的,一面唱着可兰经,一面朝着东
方礼拜。
富爱德悄悄说:“他们正祈祷和平呢。”便领我走进一间展览室,里边
摆着“解放省”各种成就的图片。她的眼睛含着梦一样的神情,望着迎面墙
上贴的一幅画儿说:“你看得见么?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未来。”
画儿上画着一个农民,从破烂的小土屋走出来,举起两手望着天空。天
上是一片云雾,云端里现出一位天使,身上披着黄、蓝、绿三色的轻纱,缥
缥缈缈的,神态很美。
富爱德指着画说:“这是理想,又是现实。15 年后你再来,你会看见我
们的农民走出贫困,迈进沙漠中的天堂:黄的是沙,蓝的是水,绿的是一望
无边的田地——有多美呀。”
而且埃及人懂得该怎样创造美。就当我在沙漠里四处参观的时候,我忽
然闻到一阵花香,又浓又甜。我跳下车,不觉惊得叫起来。请想想,就在荒
沙窝里,竟而出现一片绝色的玫瑰,岂不是奇迹!花色也多,有白的,有红的,有粉的,有紫的,鲜艳极了。花朵又大,盛开的,半开的,千朵万朵,
把花枝都压得弯下腰去。花丛里,两个年轻的花匠正在从从容容修剪枝叶。
我兴奋地走上去,连声说:“漂亮啊!真漂亮啊!”
当中有个花匠叫阿提雅。他挺含蓄地一笑,剪下两枝紫色的玫瑰递给我。
我把花插到衣襟上,大声说:“我一定把这两枝花带回北京去,让中国朋友
都看看——沙漠里的玫瑰。”
阿提雅望着我微笑,慢条斯理说:“撒莱穆、昂、立鹄!”
一位埃及朋友译道:“他说:愿你平安!”
我便照着埃及的习俗,对阿提雅扬起右手说:“谢谢你,愿你的玫瑰能
开遍沙漠。”
罗持德按按小胡子,从一旁笑道:“不用慌,朋友,这样人有本领能把
沙漠里的每粒沙子都变成金子。”
这倒不完全是笑谈。富爱德领我参观的那个村庄叫“欧马尔·沙欣”。
这是埃及一位青年学生的名字。1952 年,埃及人民为着自己民族的独立自
由,沿着整个苏伊士运河爆发起反英斗争,这个青年就是在斗争中献出自己
的生命。沙漠上的人绝不肯玷辱这样一个高贵的名字。“欧马尔·沙欣”那
种清醒的斗争意志,勇敢的献身精神,处处都还活着——活在罗持德身上,
富爱德身上,也活在年轻的花匠身上。
我把那两枝玫瑰花一直带回北京,摆在我的案头上。花干了,可是更硬
挺,永远也不会谢。记得临离开埃及时,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你对埃及的
印象如何?”我回答说:“沙漠里的玫瑰。”于是我们两人都笑了。现在写
着这篇文章,望着那两枝花,我不能不怀念起远在阿拉伯沙漠里的朋友。
“愿你平安!”
上一篇:北非之金字塔夕照
下一篇:北非之金字塔夜月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文中有些文字或数据已经过期失效,仅供学习备课参考!
电脑版地址:http://www.cgzdl.com/shuku/218/9440.html
手机版地址:http://m.cgzdl.com/shuku/218/9440.html





s.jpg)
s.jpg)